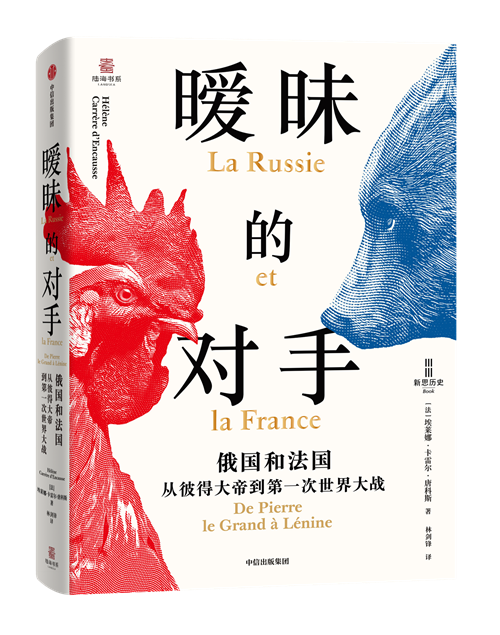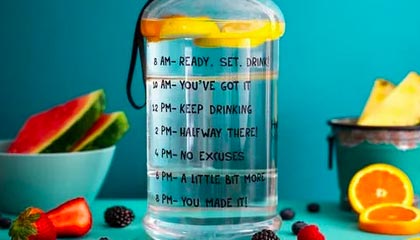数学书上有鬼:服软sc1v2星光-杨国荣︱学术上的立此存照——《故旧往事,欲说还休》读后

《故旧往事,欲说还休》,赵修义著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25年版
《故旧往事,欲说还休》是赵修义教授的回忆录。赵修义教授是我的老师,因而此书读来更有亲切感。赵老师书名所内含的深意,我不敢妄加猜度,但隐隐感到有些独特意味。
此书的副标题是“从未名湖到丽娃河”,涵盖了赵老师从北京大学求学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人生经历,但从内容看,还涉及前北大的生涯,包括儿时在抗战时期的“逃难”、在光华附中的学习生活。可以说,此书关乎他一生经历的主要人与事。赵老师出身书香门第,父亲赵家璧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贡献甚大。不过,赵老师并未附着于以上光环,而是踏踏实实地从事于哲学的教学工作。可以说,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发展历程,有其难以抹去的足迹。
记得初见赵老师,不知如何,印象中有些“病歪歪”的感觉,这可能与赵老师总是驼着背相关,但令人惊讶的是,直到现在,他依然如故,并未给人衰老之感。这也是我们感到庆幸的地方。人生之中,一些人看似强壮,但却令人惋惜地早早离世,另一些人似乎不甚健硕,但却长安无事。赵老师显然属于后者。
赵老师在教学方面很有特点。他讲课时充满激情,让人很受感染,也不敢分心。有些问题过渡时,赵老师总是能合乎逻辑地说。后来与他聊天,才知道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方面,其实是认真思考过,并作了很多努力,以便前后衔接。由此也可见他对教学的投入和用心。
1998年,按照当时制度,赵老师步入退休之列。但虽然在形式上离开教学岗位,然而学术活动他却依然积极参与。1999年,学校组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,后来此机构成为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,我被任命为所长。从研究所成立之初,赵老师就成为该所的研究人员,并参与了所里几乎所有活动。每次开会,赵老师都作为资深研究人员参加,这使所(基地)的运作增色不少。研究所是综合性的建构,涵盖文、史、哲,所里引以为豪的是,文史哲各有一位资深研究人员:王元化先生代表文学,王家范先生领衔历史,哲学中的重量级人物则是赵修义老师。思想所的建所、发展,与他们的贡献难以相分。
回到《故旧往事,欲说还休》。这一回忆录同时也折射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学术变迁。从北京大学的师长,到华东师范大学的人与事,赵老师以亲历者的身份,作了多重回忆,马寅初、郑昕、洪谦、周辅成、汪子嵩等等,这些对我们比较遥远的人物,却曾是赵老师的老师,在其笔下,他们不仅个性突出、栩栩如生,而且学术上的观点、趋向也各有特点、交相辉映。虽然以前上课时也听到赵老师的介绍,但以书面形式系统描述,还是第一次,因而印象更为深刻。
回忆录提到的哲学界往事,不仅仅关乎抽象的学术思想,而且具有时代的印记,如人道主义的讨论、科学的走上历史前台、关于劳动、收入与社会公正等问题,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伦理制衡,都已超越了观念之域,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向。关于社会公正的讨论,我也参与了其中一次小范围的讨论,记得王家范、赵修义老师都参与了,并提出中肯而深入的见解。这些活动既反映了历史的变迁,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印痕,其意义已非一般回忆文章所能范围。
从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,赵老师对华东师范大学,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专业有深厚情感,收入的文章中,涉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占了很大篇幅。在回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奠基者冯契先生的章节中,这一点特别明显。对冯契先生,赵老师既内含深情,又充满敬意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书中尤为关注冯先生在哲学领域中的工作,对冯先生主持华东地区马克思主义教材、晚年“述往事、思来者、通其道”,都作了具体的分梳。通常将冯契先生视为中国哲学史家,但赵老师以翔实的事实,表明冯先生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,这既合乎历史事实,也从一个方面对时下热衷议论的中国哲学、西方哲学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,作了具体回应:现在的总体趋向是喊口号,大谈中、西、马的结合,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做,按照赵老师的回忆,冯契先生可以看作是在实践层面实现这一结合的哲学家。
当然,作为赵老师的学生以及后来的同事,书中提及的一些人与事,或可作一些补充。承蒙赵老师不弃,书中提及我的职称晋升问题。可能作为旁观者,视域受到一些限制。我的晋升过程实际上如下:当时学校打擂台,系里将我作为副教授人选提到学校,我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情况,结果,与会的校长(袁运开)、书记,以及文理科的20多位资深专家,认为我已达到教授的要求,并决议聘我为正教授。这以后,才有赵老师书中提到的系里讨论:如果学校没有这一决定,后续的工作都失去了前提。这一过程在程序上不同往常:一般情况下,按程序职称判定先由系里教授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讨论人选,然后报到学校进一步审定,但这一次则是由学校(擂台会议)先定,再到系里,然后由系向学校申报。简言之,系到学校(系-学校),变为学校-系-学校,也可以说是“特事特办”。
另外,记得赵老师在课堂上一再提到,洪谦先生提醒他,“胆不要太大”,意思是,学术上谨慎,不要急于发表意见。这句话确实有道理,但是,如果过于慎重,也可能抑制人的创造性。我个人的主张是:打磨与打住应当统一。一方面,作出某种判断、提出新见,需要慎之又慎,提出以后要反复斟酌。另一方面,也不能在学术上“就此收手”或永无止境地考虑再考虑,因为如果不敢果断地提出创造性见解,学术也难以进步。赵老师是书中并没有提及洪谦先生的“胆不要太大”的看法,这里只是根据以往印象随意议论,并非关乎回忆录本身。
总之,《故旧往事,欲说还休》是一本很有教益的回忆录,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将留下了珍贵的材料。